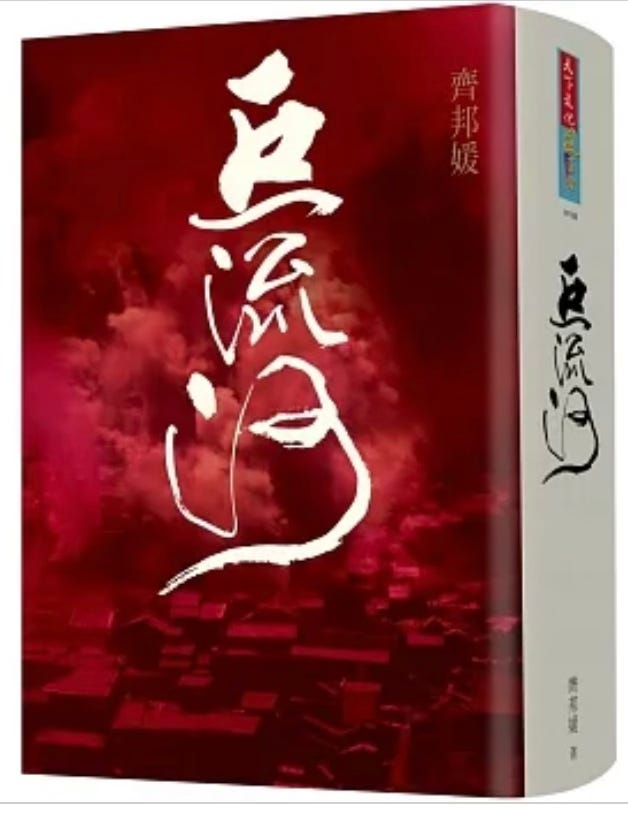西門不暗 | 《巨流河》打动人心的背后,是深沉的历史关怀
齐邦媛去世引发了两岸的悼念潮。昨天读到韩福东先生《纪念齐邦媛:<巨流河>被高估了吗》一文,是一篇很出色的文章,也让我跟随着文中的几个追问去反思:齐邦媛被高估了吗?高估的主体是谁?王鼎钧说的《巨流河》似乎没有史学抱负指的是什么。
01
先说个身边的故事。我有个朋友,日常偶尔看书,她在看完大陆出版的《巨流河》之后,几次向我借台版的《巨流河》。书是5年前借出去的,至今没有归还。我问的时候她说,几个朋友传阅之后,书到了她姐姐手里。我后来没有继续追问书的下落,让更多人看到,也许正是书的价值所在。
这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巨流河》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至于王鼎钧,我估计她们是没有听闻过的。
我在韩福东先生的文章里没有找到认为《巨流河》被高估的主体是谁,这也是我认为这篇文章在提出了一个很好问题之下的不足,主语模糊不清。是谁认为被高估了。
《巨流河》有文学化的成分,众多读者被它的文辞所打动,但它不只是个人回忆录,也不只是齐家的家族史。
02
目击成诗,遂下千年之泪。杜甫的诗句可以做《巨流河》的注脚。
齐邦媛说,她80岁开始写《巨流河》,是想记录那个有骨气的中国。
那个有骨气的中国,内含有郭松龄和齐世英,但绝不仅仅是他们这些奉系反叛的军官。书中让人动容的是以身殉国的飞行员张大飞,抗战期间在乐山教她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以及晚年在台北的钱穆。
哈佛教授王德威说,齐邦媛在《巨流河》里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奠定了她这本书的态度。这个评价恰当,但我认为,里面对周恩来、闻一多的评价,哈耶克去台湾访问的描写,潜藏的是她的史学抱负。对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的细节描写和简短的评论,闻一多的个人评价,虽然篇幅不大,都力透纸背,里面是经历了多少岁月的反思,才能让一个80岁的老人,用从容而又犀利的笔调写出来。再联系她在抗战期间对学生运动的淡漠,以及对身边同学狂热向往延安的反思,齐邦媛真如她自己所说的,不关心政治,只投身于文学?
不可否认,作为齐世英的女儿,在郭松龄倒戈一事上她有过于乐观的判断,但“渡不过的巨流河”,她绝不仅仅是用来象征自己的家族史,以及奉系军阀,乃至东北。个人回忆录的优点在于个人充沛的情感和鲜明的立场,正因为此,它不能被当过历史作品,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能超越史学著作的理性,融国家和个人家族的历史于一炉,从齐世英渡不过的巨流河来看,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多少人和他有共同的遭遇?历史由胜者组书写,但败者组的身世让历史更唏嘘,更有反思的空间。普通人有多少是想从回忆录中寻找历史真相?更多人是用他们的美酒浇心中的块垒,共情的需求远超冷静的挖掘。
03
事实很重要,如何阐述它更重要。
《巨流河》里描述的大历史,跟其他的作品并没有太大差异。它吸引人的是齐邦媛个人和国家休戚与共的创伤,是她在重要历史关头的在场感,是生命中重要的那些人,影响了她也影响了中国。许多年后,当她坐在最后的书房,她从激荡的80年人生里裁剪出来的片段,每个字看似不经意,实际上都是千锤百炼的。太多人纠结于她在郭松龄和东北战局的乐观判断,而忘了巨流河是一个文学象征,但这个象征又隐含了她对20世纪中国最大政治事件的判断,渡不过河的远不止齐世英和郭松龄,还有国民党的一众将领,还有南渡北归的一代知识分子,被战乱化为历史灰烬的草民。书里最后的哑口海虽归于平静,但青史没有尽成灰。它还活在每个具体的人的心灵里,以民族记忆的方式,有待重新发酵,沉淀,每个品过的人,感受都不尽相同。
04
在上周末的悼念中,许多人引用王德威对《巨流河》的评价: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王德威这是引用书中覃志豪的词,一种方便的类比。其实,王德威还这么评价道:《巨流河》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说来,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先生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世代总体情绪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齐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写出一代人的追求与遗憾,希望与怅惘。
《巨流河》的前半部分内容在大陆读者里引发了巨大反响,对后半部分相对平淡的章节关注不多。我周末重读了后半部分台湾的岁月,写齐邦媛回大陆的感怀,其实用意极深。人生上半场是渡不过的巨流河,人生下半场是回不去的巨流河。尤其是阔别半世纪不见的南开同学、武大同学,每次相见都让她生发出: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感慨。
05
齐邦媛在她和王德威合著的《最后的黄埔》里描述了台湾老兵的境遇:在台湾,被人称为外省人;回大陆,被当作台胞。海峡两岸,他们都是异乡人。
1995年,齐邦媛站在渤海湾北望故乡辽东半岛,她感慨:“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永远回不了家的船。”
异乡人的视角为她的作品带来了纵深感,两岸开放探亲后台湾老兵的幻灭感,只占了一小部分内容,但很能折射两岸关系,骨肉之情在政治隔阂下的疏离,团聚的欣喜很快被现实所冲刷。
台湾部分动人的段落,哈耶克访台,和钱穆先生的交往,对张学良的评价,南京空军战士陵园寻找张大飞。都可体现齐邦媛的史学抱负。再结合1949年之前的学生运动评价,周恩来和闻一多的描述,齐邦媛在政治和历史层面的立场清晰可见。
哈耶克访台,齐邦媛对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翻译,它的影响是大陆人所不能体会的。对张学良的评价,跟大陆的主流史学立场更是大相径庭。而张大飞这个人物,是许多大陆读者和二战时中国飞行员战斗史的第一次接触。这段爱情故事被搬上了银幕。但在历史层面,它虽然没有被掩埋,但始终被人为遮蔽。
觉得被高估的人,可能会嘲笑齐邦媛作为文学家在历史面前的天真幼稚,但这些人长期受意识形态的规训,对于历史有刻板和必然性的认知,不知道历史由无数的偶然性耦合,那些看似定论的岁月,虽不容假设,但还有太多反思的可能性。就是说,即使齐邦媛在奉系郭松龄倒戈上的判断不符合历史的原貌,国内史学界的判断也可能是错的。《巨流河》提供的是一种打量历史的角度,个人化但兼顾了家国视角的写作手法,历史本身没有标准答案,一本书更不可能提供符合历史原貌的定论。
06
至少对我来说,钱穆在历史关头的去留,哈耶克在政治层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论断,齐邦媛对一众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已经将她的历史观融合进了回忆录。而力图去追寻一种标准答案式的历史观,这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强迫症?《巨流河》不仅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也对历史潜藏的思潮做了梳理,她的同学们在历史的关头各自奔赴,立场上的分歧冥冥中做了命运的标记。
《巨流河》极具文字张力的呈现,使得它跟其他作品的差异分毫毕现。带有血肉和呼吸的描写,能直通中国人的心灵,那些看似学术枯燥的归纳,只能在小圈子被提及。
齐世英的一生,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这是唐君毅所说的中国文人精神。齐邦媛在父亲去世后的描述,精准了继承她父亲的遗志。
齐邦媛和齐世英的一生有诸多重合处,渡不过的巨流河,归于寂静的哑口海,父女的人生浓缩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这是两代人的历史抱负。
张大飞的一生短暂如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如此而已,却是"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那般灿烂洁净"。齐邦媛对张大飞浓墨重彩的描写,是她《巨流河》最华丽却低调的篇章,那个短暂却值得一代代人纪念的有骨气的一代人,有骨气的中国。
这不是史学抱负,又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