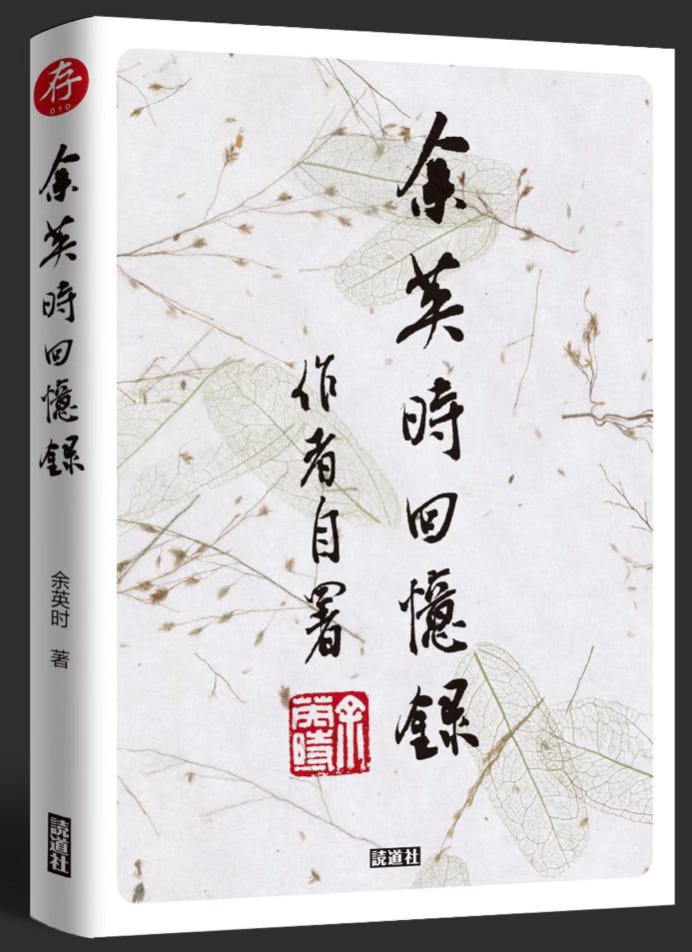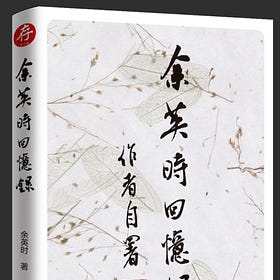廖志峰 | 开往普林斯顿的慢车:《余英时回忆录》后记
编者按:日本读道社推出他们第十本书《余英时回忆录》,本书引自台湾允晨。台版编辑廖志峰的《开往普林斯顿的慢车》记录了他与余英时教授交往及编辑《余英时回忆录》的经历。2018年,廖志峰为出版回忆录多次与余教授沟通,9月赴普林斯顿探访余教授,三天相处中畅谈人生、历史与思想,留下难忘回忆。余教授夫妇的热情款待、书房拍摄及签名诗作《河西走廊口占》成为珍贵记忆。2021年余教授去世,廖志峰深感遗憾,未及完成续编。编辑《余英时谈话录》时,他重温与余教授的对话,感受到其智慧与亲切。出版过程如马拉松,充满挫折却意义非凡,书中余教授的声音仿佛未曾远去。廖志峰感叹人生际遇,视与余教授的相遇为编辑生涯的巅峰,强调心智成长的珍贵。
本文为《余英时回忆录》编辑手记,由出版社和编辑授权刊发。
免費訂閱《波士頓書評》及相关事宜发送邮件:boshidunshuping@gmail.com,隨意打賞:Zelle,PayPal:boshidunshuping@gmail.com 用戶名:Boston Review of Books;長期支持請點擊下面訂閱,升級為付費訂閱。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今天是余英时教授八十八岁生日,上周五已有读者从海外打电话来,问《余英时回忆录》何时出版?他看到了《明报月刊》这期刊出的文摘中余教授回忆他的香港生活,感到非常兴奋。我说不准出版时间,因为还有几章还没写,他还会写多久呢?我不知道,整个改稿过程很漫长,等于重写访问稿了。书写和出版都在和时间赛跑,但时间一直跑在我前面。《时代周报》刊出一篇专文向余教授贺寿,题目是有《尊严的知识人》,知识人一词是余教授向来喜欢自称的,有一种专业专注的向度,照片是旧照片,印象中是李怀宇所拍的,那年大概是二〇〇九年吧。余教授二〇一四年回台接受唐奖颁奖,后来我有幸和余教授合照一张,至今不能忘记那握手时的感动。昭翡问我有没有打电话向余教授祝寿?我一是不敢,二是电话恐怕也打不通,我还是习惯这样安安静静地在一旁。至于,书要怎么出?恐怕还是得等了,不过,余教授都说书要交给我,我也不那么担心了,只是不知何时写完,我一定要努力撑到那时。出版是一种考验,也是一场马拉松赛跑,我始终不确定自己的跑步节奏对不对?只是希望自己维持在跑道上,不要掉队太远,而这本《余英时回忆录》就是这场马拉松的圣杯,我想我还要跑一阵子才会抵达。我一直是平凡的人,只有当我有机会做到不凡的书时,我才感受到出版这份工作的神圣,它同时也照亮了我。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意外接到余英时教授的电话。他的声音温暖和蔼,听不出岁数。他说:你别着急,我已经开始找照片了。但我怎能不着急呢?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深夜抵达纽约,严重时差,怕误了隔天到普林斯顿的火车,夜半一直醒来,住在一间百年公寓的市中心旅馆,有趣的体验,品质不佳,狭窄的单人房,卫浴共享,听着各种声音,此起彼落,是一篇小说的开端。这间建于一九三〇年代的公寓旅馆,在三楼至五楼,没有电梯,入住时已经是清晨一点了,几乎没什么睡,就起床准备前往普林斯顿,天色亮时才发现一整层竟隔成三十个小房间,房间内只有一张床和一小茶几,不能再小的单人房,像是船舱卧铺,听说以前是专供在饭店工作的人住宿的地方,我头一次觉得自己住进了作家才会住的旅馆。那么,我要写什么呢?我想起博格曼因为胃痛,半夜起来写剧本,我则是失眠,只好写脸书。天既然亮了,也不用睡了,该起来找路前往宾州车站。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六日:大学时读到《历史与思想》,对余英时教授平实易读的文字,深刻的思想,十分惊艳,也让就读中文系的我,开始有了一种历史的眼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照今天的我,是有脉络的。书上当年用荧光笔画的重点,到今天已成了咖啡色块,是时间的见证。即将离开了普林斯顿,后会难期,于是请余教授签名留念,我对余教授说:我不敢请求题字,但签名应该是可以的吧。余教授说:我知道你不会开口,但我会写给你。我只能傻笑。这次来美的机上,重读此书,仍然有当日初读时的感动。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才从普林斯顿世外桃源的仙境来到了纽约,迎来熟悉的大城气味和喧嚣。如果普林斯顿之行是梦幻,那么现在到了梦将醒阶段。住在下城的便宜旅馆,余教授曾问我有没有朋友在纽约,怎么找到住宿的地方?我说,就上网找地铁线旁的小旅馆,方便进出,他要我自己小心一点。余师母给的一大袋水果没吃完,我又拎回纽约,我那时看到了一大袋,愣住了,师母以为我要待多久?记得第一晚和两位老人家吃饭,点了一整桌菜,牛肉干丝,梅干扣肉,豆苗,烤龙虾,饼,白饭,我吓坏了。他们对我喜欢吃的,各有认定,所以都点了。也该惊吓的,太受宠若惊,到现在还没有回神。此刻,一个人在下城八楼的房间内,想着这不可思议的旅程,而楼下对面酒吧的客人,看完了足球赛刚散,纽约要进入稍为安静的时刻了。余教授说,没有想到我们一直没有这样聊过天。我说,余教授很少回台湾,在台湾,我恐怕也很难见到您。脸书上一点一滴写着这几日的心情,有些是突然想起,赶快记录下来,怕自己忘了。我见余教授时既没笔记,也没录音,深怕断了他的谈兴。余师母偶尔也加入谈话,这几天的接送,此生难忘。让八十多岁的长辈开车接送五十余岁的晚辈,我真是太糟糕了。整个三天,情绪很翻腾,又很宁静,被巨大的温暖疗愈了。离开普林斯顿时,偶然看到了几句话写在墙上,特别记下:Do JusticeLike KindnessWalk Humble人生行路的中道,无非如是吧。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九月中,一趟想了很久的旅程终于启动,一开始只是想去探望余教授夫妇,书稿是借口,行前《印刻文学生活志》总编辑初安民和副总编辑简白,要我写一篇长一点的文章,配合刊登《余英时回忆录》的书摘,顿时感到压力,我原本只想拍拍照写点短文,交差了事。我一直想我到底要和余教授谈什么呢?整个旅程被这个念头盘据心头,出乎意料地,当我踏进余教授家时,整个人被一股巨大的温暖包裹,我们敞怀畅谈,我没想到在普林斯顿的三天,我竟有完整的两天下午可以和余教授说话,如果不是担心他的体力,我第三天也想再去。余教授夫妇也连续两晚请我吃饭,师母很高兴,她以为余教授第二晚不会再出门吃饭了。我不是一个及格的采访者,没有录音笔,没有笔记,没有小抄,没有重点,一场开放式的谈话,却谈得很自在,不过晚上回到旅馆,才开始竭力写下所有记得的对话。我为什么不写笔记呢?我不想断了谈兴,破坏气氛,或许因为如此,两人都很自在吧。不过,我还是太紧张了,所有余教授问我的问题,我忘了反问他的看法,可以参照。我后来才知道,这两天的谈话,据余教授在《余英时回忆录》中的序言说的:是这几年来觉得最愉快和尽兴的一次。写给《印刻》的文章,交稿的同时,也传给余教授,果然他对题目中的“朝圣”有意见,我后来改了。人生行路,许多价值崩毁,许多人让我失望,这种朝圣的心情,何其难得,何其必要,几乎是依着这样的信念,让我走到现在。我自己也明白,当我踏上余教授家的厅堂时,我离自己的职场终点,也剩下最后几里路了,但心里隐隐也有一种放松感:我们要焚膏继晷到何时呢?又是为谁呢?这一堂的编辑课,是工作上最大的回馈,夫复何求?在我自己的编辑生涯中,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为即将出版的新书写侧记。关于摄影,我是要离开时才拍的。我对余老师说想拍余教授的书房,他停了一下说:我的书房很少让人进入,破例让我进去拍。他这样说我反而更不好意思了,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匆匆按了几张便退出来,但还好有捕捉到珍贵的片刻。
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余英时教授传来书名的题字,这次到普林斯顿没能亲手带回,师母说余教授怎么写都不满意,序也是这两天才写好。我一直在想着这次的旅行,在我的人生中,这三天有不可磨灭的位置,海伦‧凯勒写过一篇文章,《三日光明》,我想我也感受到光照进心里的感觉。余教授后来把我登在《印刻》文章题目改成:一个编辑的丰收之旅,他不想把自己拉高。我以《朝圣》为题,是因为我想起的是西班牙的朝圣之路,有人半途而废或中途亡故,我以为编辑也是苦行之路,挫折和挫败很多,能有这样的时刻,意义完足。从也没想到我会在飞机上开始写文章,而杂志等着我截稿落版付印,整个旅程提心吊胆,要看着钱包护照,还要看着相机,如果相机/记忆卡掉了,整个旅途就毁了,我的脸后来也像纽约客一样,充满防卫。我的心始终停留在拜访前的这一刻:终于坐上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的火车,展开一次想了许久却始终不曾真正踏出的旅程,火车从纽约宾州车站发车,车程约一个多小时,然而,对我来说,这段旅程,在我心里走了很久。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像以往一样,没有特别的事,很少打电话给余教授,早上打电话向余教授、余师母拜年,今年第一通电话,也担心普林斯顿下雪,怕他和师母进出困难。余老师说只有美东下雪,他们那里还好,我没问他《续编》的撰写进度,他已说了最近都在忙别的事,我就不多说了。应该还没提笔,我会继续等。像过去一样,我把《余英时回忆录》续编当成允晨文化四十周年的大事(一九八二~二〇二二),如果回首自己的编辑生涯,书是最好的见证。一边讲电话一边看着在他家拍的照片,好像我还在那张舒适的沙发坐着。前几天胡忠信大哥问:你们聊天时喝什么茶?说真的,那个当下,茶的滋味都忘了,我只想记下所有的谈话,随兴地谈,吉光片羽,一闪即逝,在余教授书房门口拍了他岳父陈雪屏教授写的墨宝:“英时近集坡公诗句放翁词句为楹帖嘱书之,未成小隐聊中隐,却恐他乡胜故乡。”意味深长。余教授只有在一九七八年回中国一次,再也不履故土,此心安处是吾乡。《余英时回忆录》出版后,我曾应读者要求印了一批毛边书,我后来不再印了,我相信余教授会希望读者能专注在书写的内容,而不是版本的猎奇,不过还是留一本给余教授收藏。
二〇二〇年一月五日:前几天做梦梦到与余英时教授和余师母同游,游憩地是一处满溢着阳光的湖边,梦醒时,十分眷恋,甚是思念。隔天打电话拜年问安,老人家也很高兴,要我找时间再访,偏偏我抽不出时间,真让人焦急。余老师说:普林斯敦今年还没下雪。我听了倒有些安慰,我想这样进出就方便多了。从事这一行最快乐的事是,不经意地遇到大作家、大学者,不断点醒你思想或生活的盲点,让你在人生理想上有了标高,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幸运之处。我所遇到的作家或学者,像余英时教授这样纵观全局,头脑清明的,真的不多。人多以名位财富衡量人的价值,但我追求心智的开阔与清明,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记得华文朗读节时,有人问台湾的出版品有没有竞争力?每个人看法不同。我只说:至少允晨文化的《余英时回忆录》,六四诸书,中国底层群像,是全球华文独家出版。而这些书会超越时代,继续流传下去。梦里总去了遥远的地方,醒来才知是梦。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一个多月前,美国东岸刮起了飓风,吹断了路树和电线杆,和余英时教授的联系就完全中断,直到刚刚才又接到余教授的电话,说线路修好了,声音温暖清晰,一如以往,才又放下了心。余老师说怕我找不到他。也是一个多月前,做梦梦到在一家书店里翻书,忽然进来了两个人,竟然是余英时教授和余师母,所以,我是在梦里去了普林斯顿吗?和余教授电话同时来的,还有余教授为《史学与传统》旧书新刊的题字,在等待《余英时回忆录续编》的同时,我就先编这本书吧。这书四十年前原在时报文化公司出版,余教授要我先和赵政岷董事长报备后,才进行编务处理。书里许多文章,今日读来,仍饶具兴味和启发。我相信有一命运的手在我的背后牵引,还不知自己终途,但我相信缘分,难以强求,顺其自然。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史学与传统》重新出版时,除了新序和请余教授题字,封面也是新作。照道理说,有了余教授的题字,过多的设计就太多余,和美编讨论时,我突然想起余教授家后院的竹子,竹子是余教授搬来普林斯顿时朋友送的,初时只有一株,我来访时已是一片幽篁,绿意盎然。余教授爱竹,竹子也是一种兴寄,符合他知识人的气节与精神,于是有了新的封面,送给余教授过目时,一下子就定案,余教授在《余英时回忆录》的序中说:许多事一言而决。于他于我,这番相遇与遭遇,都是我不曾想过的。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二〇一八年九月的美国普林斯顿之行,其实有很多情绪,一是《余英时回忆录》终于来到最后的编辑阶段了,二是这一切到底怎么发生的?三是接下来我还要再做什么书呢才能再抵这样的巅峰?我开始回望了。书的作者照片是在余教授的书房拍的,我不知他很少让人进去,但余教授还是答应了。我贸然出口要求之后就后悔了。我很快按了快门就退出来,没想到这一张是所有我拍余教授中最好的一张。很快就要三年了,我很想念那三天在普林斯顿的时光。很多读者问《余英时回忆录续编》何时出版?说真的,我也不知,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时,书就会出现,我这么想。
二〇二一年八月八日:这一生我遇到两位一九三〇出生的人,一是我父亲,一是余英时教授,我在普林斯顿时和余教授的闲聊中也聊到这个年代上巧合。父亲出生时是日本人,死时是中华民国人;余教授出生时是中华民国人,一度是无国籍人,然后是美国公民。我想的是时代。父亲的过世我心里有准备,因为是慢慢地走向终点;余教授的过世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因为我认为他会活到一百岁。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离开普林斯顿时,我本想开口向他要个随身物当纪念,我忍住了,我想我还会再来,但就这样错过了。编辑《余英时回忆录》我发觉余教授的照片太少,我也趁着拜访时多拍几张,也许续编可用。没想到没等到续编,后来就给了媒体朋友使用,我离开普林斯顿以后,两次梦到余教授和余师母,梦境场景明亮,醒后想起来是书店。每次梦后就给余教授打电话,余教授过世了,我心里另有一层哀伤,一九三〇年代的人,我终于完全告别了。在所有拍过的照片中,我最喜欢的是书房中的他,以及他走在阳光余晖的身形,那时我们走路去吃鱼面。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二〇一一年,辛亥百年,余英时教授为他的故友陈颖士教授诗集的出版,请我协助,我一口就答应了,意外地多读到余教授的文章和古典诗作,可说是额外的收获,虽说余教授的诗只是以附诗出现。余教授的古典情怀在诗中最易看到,以诗见心,若编诗成篇,就是心史了。二〇一八秋,访普林斯顿,离开前,余教授对我说:我知道你不会开口求字,所以我会写一幅给你。当然,我是回来后才收到。我那时不知道他会写什么字给我?我后来收到了,写的是一九七八年深秋时节口占诗《河西走廊口占》:昨发长安驿,车行逼远荒。两山初染白,一水激流黄。开塞思炎漠,营边想盛唐。时平人访古,明日到敦煌。那是他最后一次去中国了。关键的一年。十一年后,爆发了六四天安门事件。二〇〇五年,我出版康正果的回忆录,舍掉了余教授建议的书名:半生忧患出长安,改以《出中国记》为名,现在想来,仍是鲁莽。我仍在书里诗里读着余英时,就像他不曾离去。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昨天传真了一封信给余师母,报告韩国有出版社要出版《余英时回忆录》韩文版的事,非常意外地,师母竟然打电话来,这是自七月二十三日的电话后再度与师母说话,师母的声音依然清朗热情,只是聊到余教授时,还是可以感觉到有种迟疑,像是收住了某种情绪才又继续说。其实我也是。提到余教授,诸般情感,总又涌上心头。师母说韩文版的预付版税就不必给她了,就当成余教授给允晨的,我收下了,但这笔钱我也决定不动。我问师母:老师最后有写什么残稿要给允晨四十年?师母说:没有,他还在打腹稿。我对师母说:那我只好梦中来问了。很想知道余教授会写什么。但人生总有这样的残念。师母说欢迎我再去普林斯顿。我总是要去的,去看余教授,余师母。
二〇二一年十月八日:怀宇的《余英时谈话录》终于进入编辑阶段了,我读着校稿,字里行间是余教授不疾不徐的谈话,如在身前,情景仿如昨日,谈话录里有太多的背景线索,也又勾起我回到普林斯顿的那两个下午。我想起了我们当日没有录音的谈话,书稿有更多背景说明,关于钱钟书,沈从文,殷海光等提及的大师的印象。我也终于知道余师母第一天中午请我吃饭的地方就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我曾在电影《美丽心灵》见过这餐厅。真像梦。余教授谈到美国最好的图书馆是国会图书馆,在华府。这段话也勾起我的回忆,我记二〇〇七年三月,我到纽约参加“汉藏会议”,会后去了康州拜访孙康宜教授,以及我的作者康正果,然后又从康州搭了火车到华府拜访作家韩秀,这应该也是一趟平常的旅途,火车中途经过普林斯顿停了一下,我念头闪过:余教授就住在这里。我抵达华盛顿车站时,韩秀在出口处接我,她很兴奋地说她刚刚见到了余英时教授了,他匆匆忙忙地要去图书馆找数据。我才知道我其实和余教授搭了同一列车,前后抵达华盛顿,不免扼腕。要很多年后,我们才终于有机会面对面说话。奇妙的缘分,既短暂也永恒。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写完《余英时谈话录》的出版故事初稿,已晚上十一点了,四千字,好像很长又好像很短,就像时间的感觉。到户外走走,松松脑,安静的秋夜,街上有几个行人,一部警车,几只在公园里的猫狗,也不是无家可归,只是逗留。我喜欢夜晚的街道更胜白天,完全是回忆的空间,只有你和你自己。我一直还在二〇一八年九月的普林斯顿,那个时刻如此鲜明温暖,让我难以离开。书就要印刷了,赶在余英时教授逝世百日出版。神奇的是,你看着书就觉得他还坐在那里和你说话,如此真实。余教授的《河西走廊口占》这幅字会放在书的扉页,因为这首诗对余教授的意义非凡,有趣的是我始终不清楚为何那印章是用贴的,我再也没有机会问了。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三日:《余英时谈话录》已送印了,书出来时刚好是《余英时回忆录》出版满三年,余教授过世满百日之期。这三年中,我梦过余教授两次,场景都像是在普林斯顿的书店,书店明亮,过世后没再梦过,倒是梦见了阳光下的墓园,看不清墓碑上的名字。人生承载的记忆越来越多,自己的时间相对越来越少,懂得这个道理已是望六之年;不是才刚过五十吗?二〇一九年六月,《余英时回忆录》获第十二届香港书奖,我的胆子太小不敢去香港领奖(朋友说你以为自己很重要吗?),但还是请余教授写了书面获奖辞,至少那时,余教授还是想写完全书的……无论如何,还有《余英时谈话录》留下来,那是余教授留给我们最后最珍贵的十五堂课。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八日:今天是余英时教授逝世百日,书赶在最后一刻送到仓库,开始发送通路。当我读着书稿时,我总感觉到他就好像还坐在普林斯顿的家中,亲切的,温暖的,不疾不徐地说着话,你听得出神,不知道他何时竟走开了,声音还在空间里传荡,然后你翻开书来读,发现他就在书里,不曾离开……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我还留着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在普林斯顿中餐厅抽到的幸运饼干中的纸条,上面一张是我自己抽的,下面一张是余教授抽给我的,让我自己读。我读到时起了某种异样的心情,就好像这趟旅程是命定的,不早不晚。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A new voyage will fill your life with untold memories.《余英时谈话录》的出版时间,不在预期中,但,或许时间到了,因缘具足时就出现了,“谈话录”是个宝库,它提供深入探究的线索和路径,因为口语,更加亲切,平易近人。所以我才说这是余教授最后的十五堂课。我在普林斯顿余教授家中,我对余教授说了两次:余老师我好想留下来跟您好好念书。余教授微笑不答,转而鼓励我创作。我们当然还谈了许多不方便详叙的,这本谈话录也都有约略触及。比起财富的累积,我更看重的是自己心智的成长,在我这一生遇到的师友中,为数不少,让我觉得自己虽不足,但其实富足,这是为什么当我一个人在夜里无人的长街晃荡时,嘴角也不自觉带着笑。书已在各书店通路了,岁末读书,尤其是成书不易的书,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呢?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三日:《余英时访问记》的作者李怀宇来信,说他几天前打电话给余师母,师母说:现在读谈话录、访谈记,就好像余老师还在身边聊天一样。深有同感。怀宇的笔,真是不得了。中秋前夕梦见余老师,真是一场甜美的梦,可惜他没跟我说什么。我有机会打电话给他时,却都在忙别的事,终究是自己错过了。九月十三日不算是特别的日子,不过,二〇一八年的这一天,我在子夜抵达纽约,准备隔天早上前往普林斯顿。人生不能重来,于是在自我意识中倒带。以为启动了什么,就可以重来。并不是。我曾推开一扇重门,却一直停留在门边。于是,只剩下书和回忆了。
(原载于联合报副刊2023年7月30日、31日)
经典访谈 | 余英时:一种现代学术“典范”的建立(未删节版)
编者按:2018年4月,自由撰稿人罗小虎前去普林斯顿余英时先生家中采访,此后访谈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这是自从2014年10月余英时著作被大陆下架之后,余英时先生名字再次在大陆媒体露面。不过,当时在媒体所发均为删减本,余英时先生谈及当下大陆史学状况部分,以及一些细节被删除。8月1日,余英时先生去世三周年,波士顿书评特别刊发当时访谈的未删节版,以纪念余英时先生。此为访谈未删节版首发。